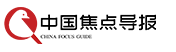“电子游戏规则”不宜认定为作品获得著作权法保护
作者:黄武双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邱思宇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一、案件情况及判决内容简述
《率土之滨》(以下简称“《率土》”)系原告杭州网易雷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易雷火公司”)自主研发、运营的是一款全自由实时沙盘战略手游,《三国志・战略版》(以下简称“《三战》”)则是由广州简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悦公司”)制作的一款沙盘策略手游。2021年5月,原告网易雷火公司向广州互联网法院起诉被告简悦公司,认为被告简悦公司的《三战》游戏,大量抄袭原告《率土》游戏的游戏内容和游戏规则,侵犯原告著作权,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原告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并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经过了长达两年的审理过程后,2023年5月15日,广州互联网法院针对《率土》诉《三战》著作权纠纷一案【(2021)粤0192民初7434号】作出了审理结果。首先,法院在分析了《率土》游戏的构成和表达后,结合2020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3条对作品类型认定开放的规则,在将《率土》游戏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认定为不同于之前类似案例中认定的类电作品/视听作品的“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的新作品进行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保护。
其次,在《三战》游戏是否侵害《率土》游戏作品改编权的判断认定中,法院对于游戏规则的表达的侵权判断规则,提出了基础游戏规则属于思想,而具体游戏规则可能构成表达,在进行电子游戏规则对比时不仅要静态对比单个游戏规则,更需要动态对比游戏规则之间的相互联系机制。因此,对于《三战》游戏是否使用了《率土》游戏中独创性游戏规则的表达这一问题,法院认定原告提出的《率土》游戏中的其中106 项游戏规则及其形成的游戏机制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表达,并将涉游戏规则划分为地图、建筑、战斗、资源、系统、赛季六大模块和《三战》相关游戏规则进行逐一对比,认为《三战》使用了《率土》其中79项游戏规则的基本表达以及游戏规则之间的相互联系机制,构成了对原告作品改编权的侵害。
同时,对于原告提出的被告侵害原告《率土》游戏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法院认为被告向公众提供交互式传播的游戏是《三战》而非《率土》,并非侵犯原告游戏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最后,对于被告应该承担的赔偿损失数额,法院提出由于原告网易雷火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简悦公司的违法所得或者其作品授权改编的使用费,法院综合考虑了原告游戏《率土》的知名度、被告简悦公司的主观故意、侵权时长及获利情况以及侵权内容对于《三战》游戏收入的贡献程度和维权费用等因素,支持了原告5000万元赔偿的主张。综上,法院最终作出了以下判决:1、被告简悦公司需要修改《三战》在案涉79项游戏规则中利用的构成《率土》独创性表达的内容,并同时修改这些规则相互联系和作用形成的游戏机制;2、被告简悦公司向原告网易雷火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5000万元。
近年来,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持续高速发展,有关游戏玩法/规则相似所导致的游戏公司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也层出不穷。在本案之前,就曾经出现暴雪娱乐公司诉上海游易公司的“《卧龙传说》抄袭《炉石传说》案”、壮游公司诉维动公司的“《奇迹神话》抄袭《奇迹MU》案”以及蜗牛公司诉天象公司的“《花千骨》抄袭《太极熊猫》案”等一系列案件纠纷。在这些案件中,法官或者将游戏规则视为思想而排除在著作权法的调整范围之外;亦或者先按照主流观点认定游戏运行动态画面整体构成类电作品/视听作品获得保护,同时游戏整体画面中游戏玩法规则的特定呈现方式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应该获得著作权法保护。
而本案中广州互联网法院创新性的拒绝将《率土》游戏整体认定为视听作品,而通过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第3条将游戏整体从现有的八种法定作品类型中独立出来,认定为一种新的作品类型进行保护,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中的游戏规则作为电子游戏独创性的核心体现,认为其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达。如此判决思路是否符合著作权法基本原理,笔者认为有待进一步的商榷,法院对于《三战》和《率土》中游戏规则的著作权侵权对比也有诸多可商榷之处,需要结合著作权法相关规则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和解构。最后,关于5000万元的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在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被告简悦公司的违法所得或者原告作品授权改编的使用费的情况下,法院作出超过法定损害赔偿数额500万元的判决存在可商榷之处。
二、关于《率土》游戏的作品构成认定
1.著作权法只可能保护“游戏规则的表达”而不可能保护“游戏规则”本身。
在本案中法院提出的一个相对争议较大的判决论点是“电子游戏规则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达而获得保护”,其论证思路在于:1.电子游戏中的具体游戏规则和游戏机制具有相对广阔的创作空间,这种创作空间留给了游戏设计者来体现其个性化的选择,存在具有独创性的可能;2.电子游戏的游戏规则和游戏机制能伴随着玩家的操作在游戏画面中以文字、图案、声音等多种形式进行动态展示,从而被玩家清晰的感知,属于以一定形式予以呈现。
首先,一审法院在论证的过程中模糊了“独创性”与“思想/表达”二分法在著作权法中的功能。著作权法作为一项近代才创设的法律制度,其目的在于保护创作者的作品内容免受未经授权的使用和侵权行为。在这个法律框架下,著作权倾向于保护作品的具体表达形式,而不是作品背后的思想或概念,这意味着著作权法并不授予创作者对其作品内容指代的思想或概念的独占权利,在判断一项作品能够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时,必须剔除这一作品所包含的抽象思想而只保留具体的表达。“独创性”也是作品的表达能够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但是电子游戏规则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并不必然意味其是著作权法意义上可以获得保护的“独创性表达”。
对于电子游戏规则的著作权法保护,张伟君老师就曾指出“法院在判断‘游戏玩法、规则’时需要注意区分‘独创性’与‘思想/表达’二分法在作品判断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首先必须是具体的表达而不能是抽象的思想,否则即使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创新思想,一个创新的游戏规则,也依然无法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一审法院在判断《率土》游戏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时,使用了较大篇幅去论述《率土》游戏的电子游戏规则所具有的创作空间和独创性情形,但并未使用足够的篇幅来论证电子游戏规则属于表达而非思想。
其次,玩家能够“感知”电子游戏规则并不意味着其属于能够被他人客观感知的“外在表达”。一审法院在论证《率土》游戏整体构成作品时指出“电子游戏规则和机制在游戏包体的代码中被静态固定,并随着玩家的操作在游戏画面中以文字、图案、声音等多种形式进行动态展示,玩家能清晰地感知并可根据指引进行不断交互,完成游戏目标。因此,电子游戏规则以及规则之间的联系所构成的游戏机制不只是抽象的思想,其拥有广阔的创作空间,在具有独创性时,应当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达。”作品需要能够被社会公众加以阅读、欣赏或感知才能够产生社会价值,因此需要通过一定的语言、艺术或科学符号的形式表达出来,才能够由《著作权法》加以保护。
但是电子游戏规则能够被公众感知并不必然代表其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具体表达,玩家在玩《率土》游戏时,其直接感受到的是游戏所呈现出游戏画面和相应的背景音乐,相应的电子游戏规则和游戏机制只不过是部分有经验的玩家对游戏画面这种直接表达的进一步感受,而且这种感受所对应的是电子游戏规则和游戏机制本身,而非他们对应的表达。袁博法官曾经指出,人们在判断游戏规则的著作权保护时,往往会混淆“游戏规则”和“游戏规则表达”两个概念,“游戏规则”指的是在玩游戏时所遵循的一套规则或准则,规定了游戏的目标、参与者的行为、胜利条件、规则执行和惩罚等方面。而“游戏规则的表达”指的是将游戏规则以某种方式明确地表达出来,以便参与者能够理解和遵守这些规则。著作权法并不保护游戏规则所包含的“规则”本身(即如何进行游戏),而只保护规则的具体表达,人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游戏规则,此时规则表达就有可能构成文字作品(例如游戏策划在制作游戏时为了方便游戏开发所制作的明确表达了电子游戏规则和游戏机制的策划文档就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具体表达)。因此,当电子游戏规则和游戏机制被固定在游戏中时,玩家在操作游戏并接触游戏画面时感受到的是“游戏规则和游戏机制”本身,而不是“游戏规则和机制的表达”,并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具体表达。
2.在现有表达形式足以认定作品时无需创设新的作品类型
在本案中,针对《率土》游戏的作品认定,法院还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即“电子游戏整体不应当被认定为视听作品,应当根据《著作权法》第3条认定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而获得著作权法保护”。法院认为,作为独创性体现在游戏规则、游戏素材和游戏程序的具体设计、选择和编排中的电子游戏,系文学艺术领域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有其独特的创作方法、表达形式和传播手段,与视听作品有本质区别,亦和其他法定作品类型存在本质不同,应当被认定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首先,表现形式是作品分类的基础因素。《著作权法》第3条所列举的8种作品就分别对应了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文字作品以文字形式表现,不配词的音乐作品的基本表现手段是旋律和节奏,美术作品以线条、色彩等来表达,视听作品则利用动态变化的连续画面来传达。因此,若想要认定一种新的作品,其前提必然是出现了一种之前不存在的新的表达形式。而对于电子游戏而言,虽然存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子游戏,同时其最终展现出的动态画面内容也因为其对应的美术、音乐等资源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究其本质,电子游戏整体仍然是以代码为具体表现形式的计算机程序为主,和其他类型的计算机程序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只是添加了相对内容丰富的素材和资源库。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软件运行通常遵循着数据库与程序相互分离的设计,即计算机程序在替换不同的数据、资源库后也能继续运行,程序本身与数据库资源库并没有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因此,电子游戏整体上并未产生与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8种表现形式不同的全新表现形式。电子游戏的运行程序以计算机软件的形式表现为代码形式的文字作品,电子游戏的对应资源库中存在的音乐、图片等元素在具备独创性时表现为独立的音乐作品、美术作品,电子游戏程序运行时调出资源库中合适的音乐、文字、图片等元素并通过液晶屏幕展示出的动态连续画面具备独创性时表现为视听作品,无需创设新的作品类型将其认定为新型作品。
虽然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将“作品类型法定”改为“作品类型开放”,在《著作权法》第3条新增了“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可以随意创设新的作品类型进行保护。著作权作为一项排他性极强的绝对权,其赋权代价在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公众行为的自由。认定新作品、提供绝对权保护,意味着对他人行动自由的限制,对此必须高度谨慎。因此,在现有表达形式足以认定作品时无需创设新的作品类型,对于“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认定时需要保持一定的克制。
三、关于《三战》侵害《率土》游戏表达内容的改编权
本案中的另一个争议焦点在于被告运营的《三战》游戏侵犯了原告运营的《率土》游戏的哪一种著作权权利。原告认为被告将《率土》游戏中包括:资源、建筑、地图、武将等数百种游戏元素整体移植到其《三战》游戏之中,导致两游戏无论是在游戏机制、元素设计还是在交互设计等方面均高度相似,以致游戏呈现的画面与带给玩家的体验整体高度近似,构成对《率土》游戏的整体抄袭,严重侵犯《率土》游戏作品的改编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法院在对比了两款游戏的和部分类似玩法的先前游戏的具体内容后,认定《率土》游戏中涉及到106项游戏规则和其形成的游戏机制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表达,而《三战》游戏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了其中79项独创性表达,构成对原告游戏作品改编权的侵犯。
1.侵害改编权的前提是使用了原作品具有独创性的表达
《著作权法》第10条第14项规定的改编权定义是“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改编行为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融入一定创造性劳动的派生创作行为。改编排除对原作品原封不动的使用以及在原作品表达基础上进行的非实质性改动,只有在保留原作品基本表达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原作品而创造出新作品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改编行为。侵害改编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未经原著作者或权利人的许可或授权擅自将原作品改编成其他形式或媒介,如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将戏剧改编成舞台剧等。落实到本案中,法院认为被告运营的《三战》游戏侵犯原告的《率土》游戏的理由在于被告在游戏中大量使用了原告属于独创性表达的游戏规则和机制,虽然在这一基础上创作出的《三战》游戏属于新作品,但是仍然侵害了原告的改编权。
然而,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具体的表达而非抽象的思想,仅仅根据原作品的思想创造出的新作品并不属于受到原作品改编权控制的行为。因此,侵害改编权的前提是使用了原作品具有独创性的具体表达。落实到本案之中,这种具有独创性的具体表达指代的是《率土》游戏中对于游戏规则和游戏机制的具体文字、图片介绍,而非具体的游戏规则和游戏机制本身。例如,《率土》游戏中的“三分归一”游戏规则,具体表达内容为“当全部13 州首府被同一个同盟占领时,获得奖励为 500 虎符。”而《三战》游戏中“天下归心”游戏规则,其具体表达内容为“当8个州府和洛阳被同一同盟占领,获得奖励为300金铢”。
2.侵权对比时需要排除公有领域的表达
改编权的核心内涵是改变在先作品,创造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同时,改编作品与在先作品之间又必须具有表达上的实质性相似,只有在保留在先作品基本表达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在先作品创作出新作品,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改编行为,否则新完成的作品因缺乏与在先作品的关联而属于独立创作完成的新作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构成对另一作品的改编,关键还是判断在后作品中的相关表达是否与在先作品中的相关部分表达构成实质性相似。因此,“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思路在判定改编行为时依然适用。
然而,改编权的“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思路与复制权并不相同。不同于将作品与复制件进行整体直接对比来判断是否“实质性相似”,在改编权侵权案件中,比对的仅为在先作品的独创性表达部分是否被在后作品中以实质性相似的方式再现,换言之应该将在先作品中独创性表达的整体与在后作品中的相应部分比对,同时在先这一独创性表达部分必须是在先作品的核心部分或能成为基本内容,能够代表在先作品给予读者独特的欣赏体验。
此外,由于作品的创作往往是需要以借鉴大量在先作品为前提,对于处在公有领域的在先作品的借鉴和演绎不受著作权法的限制。因此,在进行改编权侵权判定的对比判断时,若存在处于公有领域的在先作品表达时,需要排除掉这一部分的具体表达内容再进行侵权对比判断。落实到本案中,被告针对原告的改编权侵权诉求提出了通用设计和在先作品抗辩,列举了包括《三国征途》《三国志》《魔兽争霸》等多款游戏进行抗辩。但法院在进行侵权对比时并未详细说明具体是如何排除游戏规则内容的现有通用设计和在先作品抗辩,存在可商榷之处。
3.介绍相同游戏规则的具体表达还受到“混同原则”限制
基于著作权法不保护思想的原则,由于游戏规则本身应该被视为一种思想,其内容本身不应该受到保护,受到保护的仅仅是对内容的独创性表达。但是,如果要用简洁的语言来陈述某一套规则,则可供选择的表达方式并不多,不同的人用各自语言描述这套规则的结果总是大同小异的,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不受到保护的“思想”和原本可能受到保护的“表达”混在一起,无法在两者之间画出明显的界限。在此情况下,如果一种规则由于过于简单导致只有非常有限的具体表达,那么这些表达也会受到“混同原则”的限制而被视为“思想”不受保护。例如在本案中,《率土》中的“沦陷”是指“游戏玩家主城被攻破时,可以占领玩家土地出征”,与之类似的是《三战》中的“俘虏”同样指“游戏玩家主城被攻破时,可以通过被俘虏玩家的土地进行连地”,即使两者的具体表述存在较大的相似性,但是由于其对应的游戏规则本身(思想)相同,且只具有有限的表达,则在进行改编权侵权对比判定时应当通过“混同原则”对其进行限制。
四、5000万元的侵权责任赔偿额度计算数额是否合理
最后,法院在认定被告运营的《三战》侵害原告作品《率土》后,支持了原告高达5000万元的损害赔偿请求。但同时法院也提出,网易雷火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简悦公司的违法所得或者其作品授权改编的使用费,然而5000万元的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远远超过了法定赔偿数额上限的500万元,法院判决的这一数额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在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同样适用民法的基本原则。在民法中,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和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遵循填平原则(也称为赔偿原则),填平原则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赔偿被侵权一方的损失,使其能够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得到补偿,恢复其合法权益。根据这个原则,当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侵权人应该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失进行补偿。
著作权法中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公式也遵循了填平原则。《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由此可见,著作权法的三项计算公式对应的数额分别为:权利人因为侵权行为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违法所得以及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参照。具体落实到个案时,应当先考虑是否能计算清楚权利人因为侵权行为受到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违法所得,当这两种计算方法无法获得准确的数额时则考虑通过许可使用费作为参照计算赔偿数额。
然而在司法实践之中,由于当事人的举证困难,往往难以获得足量证据来通过以上三种计算公式计算损害赔偿数额,因此法院在最终计算损害数额是常常通过法定赔偿进行自由裁量。虽然2020年著作权法修改后大幅提高了法定赔偿数额的上限,由50万元提升到了最高500万元,但是本案中所认定的5000万元赔偿数额还是远远超过了法定赔偿数额的上限,法院判决支持的赔偿金额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支持。
五、结语
近年来,随着将游戏动态画面作为视听作品保护这一共识的逐渐成熟,游戏竞争者将重心放在了游戏玩法、机制之上。伴随着大量的“换皮游戏”的出现,以游戏规则、游戏玩法为著作权保护核心争议案件也层出不穷,意味着游戏行业白热化的竞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虽然“抄袭”“制作换皮游戏”等行为看上去令人不耻,但著作权法有其内在的立法目标,在保护创作者合法利益的同时也需要留下足够的、可借鉴的公有领域素材,从而促进源源不断的创作。游戏的规则、玩法和机制本身属于思想层面的产物,若对其进行作品保护的话会过度压缩社会公众的行为自由,带来的危害远大于益处。制作“换皮游戏”的行为,应当考虑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维护相关权益,而非寻求突破著作权法原理的方式认定游戏规则构成作品进而获得著作权法保护。
注释:
1.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22号判决书。
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054号民事判决书。
3.张伟君:《呈现于视听作品中的游戏规则依然是思想而并非表达——对若干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判决的评述》,载《电子知识产权》2021年第5期,第71页。
4.广州互联网法院(2021)粤0192民初7434号判决书。
5.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6页。
6.袁博:“《三国杀》曾因这个问题惹上大麻烦:游戏规则受法律保护吗?”中国知识产权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DI3NjAyMg==&mid=2649658321&idx=4&sn=42f111a5c3425d1218d653f935cba37b&chksm=87187e08b06ff71e54789008471f09e53153c9804d9a79a4db1573e0f855a6a26699f6fe4be1&scene=27.
7.网络游戏规则可版权性问题分析,刘鹏、王迁,中国法院网,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12/id/4750526.shtml.
8.广州互联网法院(2021)粤0192民初7434号判决书。
9.陈锦川:网络游戏是一种独立于其他作品的新的作品类型吗?——从网络游戏借以表现的形式说起,https://mp.weixin.qq.com/s/phfki4ntUXDNxoW3dGaQPg.
10.王迁:《论作品类型法定——兼评“音乐喷泉案”》,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第12页。
11.王迁:《<著作权法>修改:关键条款的解读与分析(上)》,载《知识产权》2021年第一期,第23页。
12.李杨:《改编权的保护范围与侵权认定问题:一种二元解释方法的适用性阐释》,载《比较法研究》2018第1期,第71页。
13.张玲玲,张传磊:《改编权相关问题及其侵权判定方法》,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8期,第33页。